
歌劇《漂泊的荷蘭人》為國家大劇院揭開了向瓦格納誕辰200周年致敬的盛大序幕
4月28日晚,國家大劇院2013年歌劇節(jié)迎來了一部重磅大戲,歌劇《漂泊的荷蘭人》繼2012年成功首演后,被再度搬上舞臺(tái),不僅由多位世界一流歌唱家領(lǐng)銜的演出陣容大放異彩,指揮家呂嘉所帶領(lǐng)的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tuán)更是獲得好評(píng),而意大利金牌導(dǎo)演強(qiáng)卡洛·德·莫納科打造的“3D”魔幻舞臺(tái)則讓觀眾再度領(lǐng)略到這部歌劇的深刻魅力。隨著“荷蘭人”第三輪演出的成功演出,國家大劇院也由此揭開了向瓦格納誕辰200周年致敬的盛大序幕。
以上是新聞媒體的報(bào)道,這部魔幻史詩大劇在專業(yè)人士看來演繹的很震撼,視覺與聽覺的沖擊力再度給予觀眾無窮的想象力。但在大多數(shù)非西方人看來,《漂泊的荷蘭人》并沒有讓他們有強(qiáng)烈的感官享受,非西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以及西方歌劇在非西方國家還不是很流行的當(dāng)今,欣賞西方歌劇就成為非西方人必須認(rèn)真思考的問題了。

電光火石般閃耀的音樂,亦真亦幻的舞臺(tái)效果延續(xù)了2012年首演時(shí)的盛況
歌劇在文藝復(fù)興時(shí)產(chǎn)生于意大利佛羅倫薩。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意大利半島是歐洲文化的發(fā)動(dòng)機(jī),意大利語是當(dāng)時(shí)最為通行的語言。而意大利語由于每個(gè)單詞及其變位后的結(jié)束音節(jié)都是元音,因而發(fā)音響亮,利于歌唱。其后的閹人歌手與美聲唱法能夠在意大利誕生也與語言有關(guān)。而且,懷抱復(fù)興古希臘戲劇觀念的拓荒者們希望能用音樂來講故事,而那時(shí)的主要歌劇題材都和宗教有關(guān),因此,清晰明了并感人的敘事功能成為歌劇的特點(diǎn)。可以說,歌劇是一門用音樂來表現(xiàn)戲劇的藝術(shù)樣式,也就是說在歌劇中,戲劇第一位,音樂第二位。
自歌劇肇始,按照年代的順序通常分為4個(gè)時(shí)期。即:巴洛克時(shí)期、古典時(shí)期、美聲和浪漫時(shí)期、真實(shí)主義時(shí)期與現(xiàn)代歌劇。
歌劇的第一個(gè)輝煌出現(xiàn)在巴洛克時(shí)期。以亨德爾(1685—1759)的歌劇為代表。其后經(jīng)過眾多作曲家的努力,歌劇進(jìn)入古典時(shí)期,在莫扎特的時(shí)代步入第二次輝煌,尤其以他的晚期4部歌劇《費(fèi)加羅的婚禮》、《唐璜》、《女人心》和《魔笛》(1786—1791)為代表。第三個(gè)時(shí)期,美聲和浪漫時(shí)代的歌劇,以羅西尼的《塞爾維亞理發(fā)師》、貝里尼的《諾爾瑪》和多尼采蒂的《愛情靈藥》為代表。1850年以后,意大利語歌劇的標(biāo)志性人物威爾第的《納布科》、《弄臣》、《茶花女》、《阿依達(dá)》、《命運(yùn)之力》和《奧賽羅》與德語歌劇的劃時(shí)代人物瓦格納的歌劇《湯豪塞》、《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指環(huán)》,將歌劇藝術(shù)推向歷史最高點(diǎn)。第四個(gè)時(shí)期,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歌劇由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領(lǐng)銜進(jìn)入真實(shí)主義時(shí)期,代表作品有《波西米亞人》、《托斯卡》、《蝴蝶夫人》和《圖蘭朵》等,并在歐洲各國家和民族間發(fā)揚(yáng)光大,緊接著由法語歌劇《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作曲德彪西)、德語歌劇《莎樂美》(作曲理查·施特勞斯)、英語歌劇《皮特格雷姆斯》(作曲布里頓)等催生了一系列現(xiàn)代歌劇的產(chǎn)生。
可見,作為西方核心藝術(shù)形式,歌劇具有高度濃縮、高度綜合、高度技巧的特點(diǎn)。如何欣賞歌劇,對(duì)于非西方的觀眾一直是一個(gè)難題——非西方人觀眾會(huì)發(fā)現(xiàn)欣賞一場歌劇的演出很“累”,需要?jiǎng)幽X子和調(diào)動(dòng)各種神經(jīng)感官,并在智力上與舞臺(tái)表演一起完成戲劇的進(jìn)行。
首要原因是劇情和語言的隔閡。歌劇演出用原文演唱,現(xiàn)場翻譯字幕則是欣賞的瓶頸,對(duì)于現(xiàn)場觀眾而言,要在瞬間記住冗長的外國人名,跟隨復(fù)雜的故事情節(jié)看字幕,并感受音樂的變化,確實(shí)是一個(gè)挑戰(zhàn)。同時(shí),中外文化不同,表達(dá)情感和戲劇理念的方式不同,國人總會(huì)有難以入戲的感受。
其次,非西方觀眾不習(xí)慣用音樂來理解戲劇的進(jìn)行。由于音樂習(xí)慣不同,西方歌劇中的音樂在表達(dá)戲劇進(jìn)行時(shí)往往輕視旋律、重視樂隊(duì),更多從和聲、節(jié)奏、音色等方面暗示戲劇進(jìn)行。這與國人對(duì)于音樂旋律的渴望形成了欣賞矛盾。歌劇中,人物感情脈絡(luò)的變化和國人的情感訴求也不一致,再加上歌劇故事里的西方歷史、宗教和神話的背景,對(duì)于一般觀眾而言是一個(gè)極高的門檻。
因此,作為非西方觀眾,欣賞西方歌劇,首先要做到的是提前熟悉劇情,并對(duì)主要人物的唱段和主導(dǎo)動(dòng)機(jī)提前進(jìn)行了解,這樣在現(xiàn)場就不會(huì)捉襟見肘。如果有條件能夠閱讀原文字幕,體會(huì)作曲家是如何潛心創(chuàng)作每一個(gè)字詞,再加上對(duì)于美聲唱法中的各種聲部,如女高音、男高音、女中音、男中音和男低音不同的表達(dá)方式的感受,筆者相信一定會(huì)受益無窮。
對(duì)于優(yōu)秀藝術(shù)的感知,不能采用“廁所讀物”的方式,或者所謂文化休閑和文化消費(fèi)的方式來獲得,而要理解人生獲得美感是一條艱辛的道路,唯有學(xué)習(xí)和通過深刻的藝術(shù)體驗(yàn)與必要的欣賞準(zhǔn)備才能真正感受到藝術(shù)的偉大,進(jìn)而體會(huì)人生的甘苦。
歌劇的歷史是由偉大的作曲家、戲劇家和他們的偉大作品構(gòu)成的。其實(shí)這些偉大的藝術(shù)家和你我一樣,都是經(jīng)歷了生老病死和感情折磨的普通人。他們的偉大在于通過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劇中的人物達(dá)到不朽。這些劇中人物的形象和他們的命運(yùn),不僅僅是他們那個(gè)時(shí)代的代表性人物,同時(shí)也是超越了那個(gè)時(shí)代的英雄。所有的觀眾正是通過對(duì)這些人物的了解,對(duì)這部作品的欣賞,從而體驗(yàn)了“不朽”,并將這樣的情感“移情”到自己的身上,為平凡的人生找到藝術(shù)和智慧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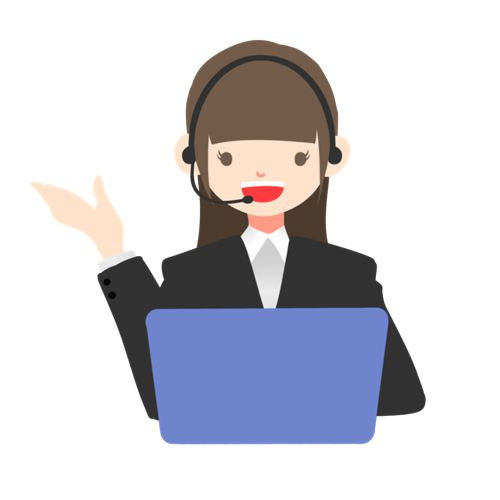

 180
180





